转自凤凰大语文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实在太火了,宋朝大词人朱东儒,他也开始学说上海闲话(hai wo)了,你不相信,我拿他一首词的结尾把侬看看:
伊是浮云侬是梦,休问家乡。
——宋·朱敦儒《浪淘沙·康州泊船》
(友情提醒,结尾处有这首词的沪语版,欢迎接龙)
这句词使用了上海方言中典型的人称代词“伊”和“侬”,而且是并列使用,强化了“沪语”的语感,如果不说明这是北宋朱敦儒写的,有的人可能怀疑这是清末民初流行于上海、苏州的言情小说系鸳鸯蝴蝶派的话语。
老克勒(old clerk)朱敦儒,他竟然说上海闲话,这是为什么呢?今朝,爷叔(“耶叔”)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侬”和伊”是上海话中最常用的人称代词,分别指称“你”和“他/她”。
“侬”和伊”这两个字,在古汉语中出现很早,但“伊”和“侬”的代指比较混乱,以下简单梳理一下这两个字作为指示代词的演变:
先说“伊”。
作为指示代词的“伊”,在上古文献中属于下巴一翘的“远指”,相当于“那个”“那里”,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秦风·蒹葭》),” “伊人”就是可见而不可及的远方那一位美人。
但古汉语中,“伊”也可以用作第二人称,相当于“你”,如《世说新语·品藻》载:“蓝田曰:勿学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唐宋以后,“伊”字用作第三人称日益成熟:
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薛蟠因伊倔强,将酒照脸泼去。(见《红楼梦》第九十九回)
再说一说“侬”字含意的演变。
关于“侬”字所指也比较乱,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定。
“侬”在古汉语中已经可以用作第二人称代词“你”,如杨维桢《西湖竹枝集》第四首诗云:
“劝郎莫上南高峰,劝侬莫上北高峰。”
“侬”也可以用作第一人称,等于“我”,如唐·李白《横江词》云:“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
吴语和闽语中,人称代词后面还都可以加“侬”,比如“我侬”,“而侬”,“渠侬”,表示“我们”“你们”“他们”。
有专家认为,“侬”来自“农”,“侬”是“农”“人”的合写。古代大家都是农民,所以,谁都可以被称为“农(侬)”。
古汉语中,泛化的人称代词其实是不发达的,我们缺少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关系亲疏,都可以统一称呼的代词,古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大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暗示性指引功能。
比如,虽然第一人称有“吾”“我”“予(余)”,但我们更多使用有表态性质的代词,如“朕”就高高在上,后来只能皇帝一人能用了;如“仆”“愚”“牛马走”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但开口就定了谦恭腔调了,定下了俯伏式交往的姿态。
第二人称代词也有“女”(汝)“尔”“若”“而|”“乃”,但如何使用,语法功能是什么,缺乏标准指引,连大文人也是随心所欲,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倒是以敬称代替第二人称的使用比较清楚,如“陛下”“大人”“君”“子”等等,用的明明白白,有头有脸。
第三人称更虚弱,要用第三人称的时候,大多是用其人的字、号,官职,地望,排行等。
上海话把“伊”和“侬”这两个代词选出来,固定为第二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不但统一了代词称谓,有利于语言的规范,无形中也普及了人民的平等意识。至少,在人称代词的使用上,“上只角(goo)”和“下只角”平起平坐了;“乡下头”的“小赤佬”“罗宋(白俄)瘪三”“戆头”和进出“和平饭店”的“大亨”“小开”“先生”也是众口一词了。
当然,上海话本身还处在动荡和形成期,就像上海的滩涂还在衍生一样。虽然,《咬文嚼字》编辑部的办公室就在上海,但对上海方言的研究并不发达,加上上海是移民城市,不断潮涌进大批“外乡人”,带着他们自己的腔调和对上海方言的个性化理解,因音成字,就出现了很多只能凭语音判断意思的上海话薛定谔词汇。
到了北京,大家都会努力朝普通话标准靠拢,会说北京土话也是光荣。对上海话,大家都不怎么当回事,那么多大亨、大资本家来到上海,带进了外语和各种方言,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资金,这是上海的光荣,也是上海的尴尬。上海本土人就开始三分之一洋泾浜,三分之一普通话,再加三分之一的沪语开始交流了,本地方言越来越不纯正。
唯一相对固定的称谓就是第二人称代词“侬”,只要加了个“侬”字就是会说上海话了。所以,《繁花》中的范老板为了表示自己已经是“上海帮”、南京路新贵族,到处用“侬”字。
朱敦儒的这首词如果只用一个“伊”字或“侬”字,还不一定有今日上海话的感觉,但两个连用,而且是“伊是…侬是…”对举的句式,就很像现代上海人讲话的腔调了:
侬要吃茶,伊要吃咖啡,我听哪人(na ning)啊?
侬是啥人,伊又是啥人?
侬去叫伊来。
侬看,伊垃拉来了。
这时候,我们若把“伊是浮云侬是梦”放到这种对话场合,是不是很像上海石库门里走出来的大小姐说的话语?
感觉到朱敦儒这句词类似现代汉语的上海话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这句词中的“是”已经用作判断词(系词,to be),这也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特征。
古汉语中“是”主要用作指示代词,等于“这个”,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孟子·告子下》),“是人”等于“这个人”。
虽然汉以后已经有用“是”作为判断词(系词)的例子,但都是误打误撞,其实很不发达,而朱敦儒这句词中的“是”完全可以判定为“判断词”,也就是“to be”系动词。
还有一个审美判断。
上海话公认是温柔敦厚的语言,有人调侃为“娘娘腔”,有人为“娘娘腔”抱不平。我认为,无需抱不平,“娘娘腔”应当用作褒义词,上海是现代文明最早落户的国际化都市,最早倡导并落实男女平等,很早就有新生活模式,比如女人可以在外上班,做白领,做领班,男人在家“买汰烧”(即买菜、洗菜和烧菜,指居家下厨的一整套流程),这在传统势力深厚的城镇简直不可思议。而上海男人乐此不疲,“男为悦己者厨”,现在,很多大城市的男性也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弱势”,这是进步,并不可笑。
我们甚至可以用“娘娘腔”的程度来判断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展。世界上某些地区,某些部落毫无“娘娘腔”,毫无娘娘地位,那是什么区,大家心里明白。
我说朱敦儒词有上海话风格,也因为这首词有点“娘娘腔”。其实,宋词本身就有一点“娘娘腔”,也就是婉约美。婉约美是一种高阶文明,大家心知肚明。宋金对峙之际,即使秉承了铁马冰河暴风雪性格的女真人,也对“娘娘腔”高看一眼。所以,金主完颜亮看到了柳永描写杭州富庶之词:“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这种“娘娘腔”的生活,激起了完颜亮的妒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见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因为,他也想带领漠北人民过好日子啊,谁不想过上“娘娘腔”的日子啊?!那是三代富贵才能熏陶出来的,女真人民要等到清人入关才能完成这个过渡。
最后,我想请AI机器人把朱敦儒的词翻译成现代近体诗,但Chat GPT的翻译不敢恭维,我截屏在下面,有空时您瞄一眼:
宋·朱敦儒《浪淘沙·康州泊船》原词如下:
风约雨横江,秋满蓬窗。个中物色尽凄凉。更是行人行未得,独系归艎。
拥被换残香。黄卷堆床。开愁展恨翦思量。伊是浮云侬是梦,休问家乡。
IT翻译截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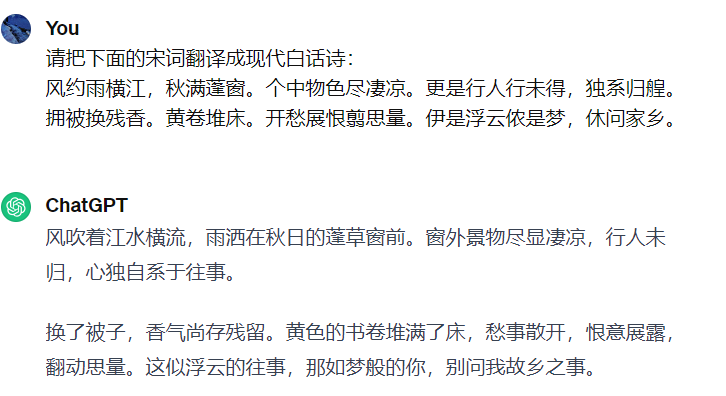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我总喜欢挑AI的刺。最近,我以“娘娘腔”特有的文明态度自我反省了一下,发现我是把它当助手了,同时,也将“伊”视为对手了,看到它不如我,窃喜之余,我就自己重新炫翻一遍如下:
风裹着雨横扫大江,秋色漫缠着斑驳蓬窗。个中物色,怎凄凉二字能清场。行人留不得也走不得,独自收系归舟小艎。
裹起被子,忘却秋寒,换了残香,续添心香。青灯照壁,黄卷满床,剪却愁恨,铺排思量。他本浮云你是梦,休问家乡。
随后,似乎没过瘾,就弄了盘小菜,喝了杯小酒,我又把朱敦儒的这首词改写成沪语版如下:
结棍个风夹(ga)着结棍个雨横扫黄浦江,拎弗清个秋色洒满茅草窗。个中光景,一塌刮子都是凄凉。阿拉想走又走不脱,独自敲着木舟咣当咣当。
裹紧被窝,换掉捣糨糊个断(dou)香,黄卷铺满了床,彻那(che na)个愁恨,赶也赶不脱,那就弗要多想。伊是浮云侬是梦,不要再问他老浜下只角有房没房。
朱敦儒,抱歉,一翻译,把您打扮成“老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