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书城》2021年4月号 一九二四年九月,杭州雷峰塔倒坍,鲁迅闻之,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前一篇从弹词《义妖传》里白蛇娘娘在水漫金山后被法海和尚装在一个小小钵盂里镇压在雷峰塔下的故事传说出发,欢呼被压迫的白蛇娘娘终于获得解放,嘲笑多管闲事的压迫者法海和尚受到玉皇大帝的追捕而躲在螃蟹壳里,非等螃蟹断种的那一天才能出来;后一篇则从报上所载雷峰塔倒坍的原因说起:“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从而引申出一些深层的文化思想问题,其中就提出了十景病的病症:“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接着,又将十景病和美学上的悲喜剧问题联系起来,说: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会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美学思想本来就是社会思潮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并不是某种哲学范畴单纯的演绎。鲁迅从十景病这种社会病态出发,进而探讨悲喜剧缺失的原因,正是从社会思想出发来研究审美特征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
十景病从何而来?这与社会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有关。
中国的社会思想本来并不封闭。老子就很看重“无”的作用,将“有”与“无”这两个对立物看作相互依存的统一体。说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且还具体指出“无”的作用:“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则更是上天入地,浮想联翩,还特别喜欢描写那些骈拇枝指、附赘县疣、啮缺佝偻的畸人。孔子则比较古板,他讲礼,规矩甚多,《乡党》一章所列的种种,就使你难以应付:“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群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待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就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森严,社会结构也就封闭起来。儒者所看重的不是有无互补,也不欣赏残缺之美,而追求十全的社会理想。特别是科举制度推行以后,更给儒者一个向上攀爬的幻想,于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相公中状元”的套路就流行起来。这种十全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清人夏敬渠所作的《野叟曝言》。这是一本长达一百五十四回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个文武兼备、无所不能的全才人物文素臣。他“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宛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闲涉岐黄,肩随仲景。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此人不但本领高强,而且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尊崇,号曰“素父”,姬妾罗列,儿孙满堂。其母水氏百岁大寿,六世同堂,皇帝赠联,七十国献寿,真是极人臣荣显之事,是高、大、全的典范。如此一来,连崇尚性灵的幽默大师林语堂也赞赏起来,还特地向读者推荐此
,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群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待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就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森严,社会结构也就封闭起来。儒者所看重的不是有无互补,也不欣赏残缺之美,而追求十全的社会理想。特别是科举制度推行以后,更给儒者一个向上攀爬的幻想,于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相公中状元”的套路就流行起来。这种十全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清人夏敬渠所作的《野叟曝言》。这是一本长达一百五十四回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个文武兼备、无所不能的全才人物文素臣。他“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宛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闲涉岐黄,肩随仲景。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此人不但本领高强,而且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尊崇,号曰“素父”,姬妾罗列,儿孙满堂。其母水氏百岁大寿,六世同堂,皇帝赠联,七十国献寿,真是极人臣荣显之事,是高、大、全的典范。如此一来,连崇尚性灵的幽默大师林语堂也赞赏起来,还特地向读者推荐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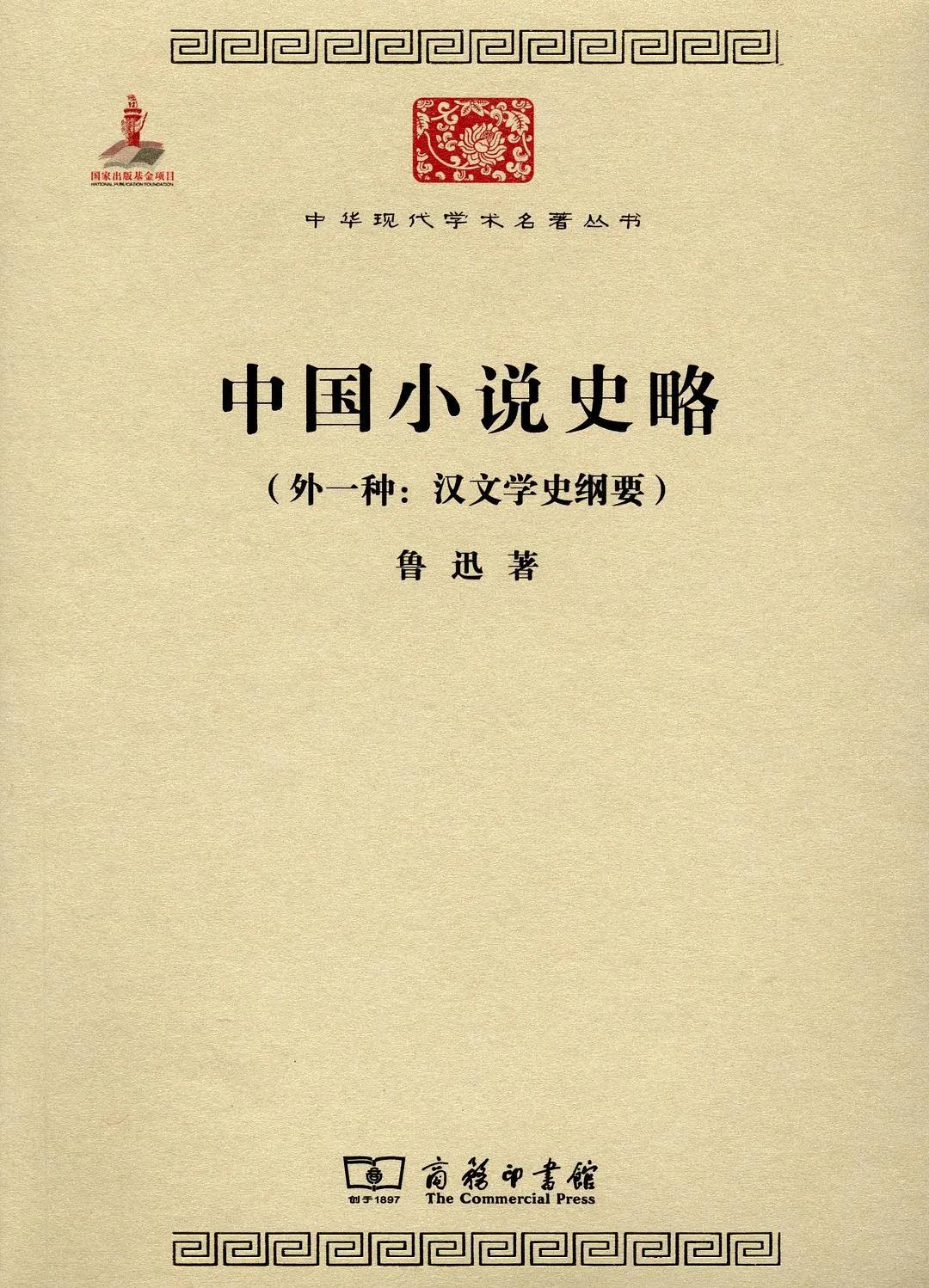 书,真不知他的“性灵”背后原是“热衷”,抑或只是“寻开心”而已?而鲁迅则认为,此书“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中国小说史略》)
书,真不知他的“性灵”背后原是“热衷”,抑或只是“寻开心”而已?而鲁迅则认为,此书“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其实并不缺少悲剧性题材,只是因为十景病作怪,就都改编成大团圆结局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故事里,杨玉环是个悲剧性人物。她原是唐明皇李隆基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被李隆基看中,夺过来做自己的妃子。这种夺媳为妻的事,历史上也有过,如楚平王就干过同样的事,伍子胥的父亲提出谏议,却被满门抄斩,伍子胥逃到吴国,兴兵报仇,演出了很有名的故事。但李隆基夺媳为妃,却没有遭到非议,反而成为千古佳话。其实,杨玉环只不过是李隆基手中的玩物,到了危急关头,就把她抛出去处死,以平息众怒,待到事过之后,再来请方士招魂怀念。这种只求自保,而以对方的性命做代价的做法,怎么能说是痴情呢?最初将这个悲剧题材编成爱情故事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叙事诗《长恨歌》。这里,根本就不提夺媳为妃的事,只说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好像是直接从民间选来似的。接着就渲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似乎唐明皇的怠政腐败,酿成安史之乱,都是杨玉环造成的。因而,他们逃到马嵬坡前,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玉环,也就有了合理性,而李隆基虽有皇帝之尊,对爱妃感情深切,但也无可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接着,后半段就大写李隆基的思念之情。还在蜀中避难时,他就天天思念:“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平乱之后,回到长安,更是触景生情:“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于是,通过方士招魂,带来钗钿信物,而且示以两人的密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借此知道玉环已归仙班。最后感叹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真是永恒的爱情呀!
以后续写这个题材的作品很多,最有名的有陈鸿的《长恨传》、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和洪昇的《长生殿》,基本上都是沿袭着《长恨歌》的路子。前两篇虽然或多或少提到杨玉环来自寿王府,但对李隆基并无谴责之意,《长生殿》则根本不提寿王府的事,只是说:“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丰姿秀丽。卜兹吉日,册为贵妃。”好像她直接选自民间,本来就是唐明皇后宫的宫女似的。这是剧作家为了要突出描写一场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有意将夺媳的丑闻加以回避了。
这一题材直到现在还在不断重复改编,说书、唱词和戏曲节目都层出不穷,但基本情节不变,只是将爱情写得更浓烈一些而已。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鲁迅,就对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别样的见解。他写过一篇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其中说道:“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而且,他还曾考虑过以杨贵妃为题,写一本历史剧或历史小说,对这个传统题材,作出不同的表现。他曾对几位朋友和学生谈过他的构思,说得相当具体。许寿裳回忆道:“他的写法,曾经说给我听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上去,把他的一生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说明皇和贵妃的爱情早已衰竭了,不然何以会有七夕夜半,两人密誓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那里会想到来世呢?”(《鲁迅的人格和思想》)郁达夫回忆道:“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然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历史小说论》)据孙伏园的回忆,鲁迅计划要写的,是剧本《杨贵妃》,他说:“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杨贵妃》)一九二四年,鲁迅还借到西安讲学之机,想作些实地考察,但结果却大失所望。他后来在给日本友人信中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信)当然,这是笑谈。一部构思多时的作品,经过实地考察后,反而停笔不写,必有深层原因,不过他没有详说。
在我国古代文艺作品中,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曲,这种回避真正悲剧冲突的作品还很多。它们常用的手法,是以大团圆结局来冲淡现实的严酷性,使读者、观众的心灵得到安抚。
《窦娥冤》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有名的悲剧,的确感天动地,但结末处却来了个当初抛下她上京赴考,现在做了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父亲窦天章,为她平反申冤,这就削弱了该剧的悲剧性,多少百姓都是冤沉海底,哪有这么幸运?作者关汉卿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作家,他自称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但毕竟是在科举制度下生活的文人,未能完全摆脱以应试来改变命运的幻想。更有甚者,后来的文人,对此还不满足,硬要将故事重新改写,变成大团圆结局,这才觉得心安理得。《金锁记》就将基本情节改变,写窦娥行刑时天降大雪,提刑官大为惊骇,赶快刀下留人,保全了窦娥性命。窦娥的丈夫蔡宗昌也没有夭折,而是赴京途中在黄河溺水,被龙王招为驸马,后来状元及第。窦天章为窦娥平反冤狱后,夫妇终于得以团圆。这样一来,这出戏就一个铅钱也不值了!
王昭君故事,也是流行的悲剧题材。马致远的《汉宫秋》写的是秭归农家女王昭君被选入宫,因为宫女太多,汉元帝来不及遍看,命画师毛延寿将她们画像进呈。毛延寿借机索贿,王昭君为人正直,不愿意行贿,而且家贫,也无钱可贿,于是被毛延寿在画像上加上一点黑痣破了相,一直得不到皇帝眷顾。后来有一夜,她寂寞弹琵琶,被汉元帝听见,前来相会,发现是个美人,遂要追杀毛延寿。毛延寿逃到前来求亲的匈奴单于处,唆使他要娶美人王昭君。汉元帝虽然舍不得美人,但为了免动干戈,还是忍痛割爱,送出王昭君。王昭君虽然答应北去和番,但还未出汉界,就投水自尽了,令人看了,不禁唏嘘!这故事不断改编,到后来,王昭君竟被写成和番大使,高高兴兴地到匈奴去做团结工作,连悲剧的影子也不见了。
孔尚任的《桃花扇》,写南明君臣的腐败和灭亡,写复社君子的抗争和失败,剧中人自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但最后,还是要加上一出安慰性的幻景:一些正义人士逃到山中,请法师设坛祭奠,只见自缢于煤山的崇祯皇帝、甲申殉难诸臣和南明的抗清英雄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均位列仙班,而南明奸臣马士英则雷劈台州山中、阮大铖跌死在仙霞岭上,终于体现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也是一种团圆结局。
在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中,悲剧性最强的要算《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所听到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就是作者对于全书的构思——但人物的命运,也都是生前注定的。最后一支《飞鸟各投林》道:“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写的是全书的结局。但可惜原作者没有写完全书就逝世了,续作者将全书完成,使读者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读,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但结局显然走样了,并没有写出“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是“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对此,鲁迅曾加以批评道:“《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论睁了眼看》)
这种大团圆结局,不但遍布于悲剧作品中,而且还渗透到喜剧作品中来。
喜剧以讽刺见长。在我国,起源可谓很早了。《史记·滑稽列传》就写过一些先秦列国的俳优故事。这些俳优是给君王消闲解闷的,但常常能通过喜剧性的言辞,对君王进行讽谏。所以讽刺性应该是喜剧艺术的特点。但后来的喜剧作品,却由于十景病的感染,讽刺的因素削弱了,而大团圆的结局却成为一个公式。

白朴的《墙头马上》是舞台上常演的剧目。剧本描写洛阳总管李世杰之女李千金春日在后花园游玩,看到墙外骑马而来的美少年裴少俊,他是工部尚书裴行俭之子,奉命到洛阳选拣奇花异卉,买花栽子。两人墙头马上,一见钟情,当晚就私下约会,随之李千金即跟着裴少俊私奔。但裴行俭家教甚严,裴少俊将李千金带回家后,不敢禀明父亲,只好私藏在后花园里,生儿育女,达七年之久。却因老子偶尔游园,撞见两个小孩,事情这才被揭穿。裴行俭坚决不容这个来历不明、私下投奔的儿媳。硬是将夫妻母子拆散,留下了孙儿孙女,赶走了儿媳。李千金回到洛阳家中,父母已亡,只好孤单度日。这本是悲剧情节了,但忽然剧情一转,裴少俊中了状元,而裴父也发现被赶走的儿媳原来是洛阳总管李世杰之女,而且当初还曾经与自己儿子提过亲,这就与儿子一起来迎回儿媳李千金。李千金鉴于辛酸往事,坚决不肯回去。最后是儿女恳求,李千金看在儿女的情分上,才回到了裴家,于是大团圆结局,悲剧变成了喜剧。但这样一来,却大大削弱了剧作的感人程度。所以后来舞台上经常上演的,只是开头部分墙头马上一见钟情那一段折子戏,表现了少男少女的青春情怀,后面那些大团圆老套,就都不演了。
此外,还出现了一种“歌颂性喜剧”,即将喜剧的讽刺性能换作歌颂性能。最常见的是《李逵负荆》,写黑旋风李逵一日下山,来到王家酒店喝酒,闻知酒家女儿满堂娇被宋江抢去做压寨夫人,就认定宋江做了坏事,回到梁山,大闹忠义堂,并押着宋江到王家酒店辨认。结果证明是别人冒充宋江之名干的坏事,同时又抓到了案犯,弄清了事实真相,借此宣扬了宋江清正廉明的形象,所以被称为“歌颂性喜剧”。但其实,这出戏的可看性,不在于表现宋江的清正廉明,而在于突出了李逵正直、鲁莽的性格,因而仍具有喜剧的讽刺性,它讽刺的是李逵的鲁莽性。
中国社会思想中的十景病,到了五四时期才认真加以清理,而大团圆结局,也是那个时期出现的新文学才予以突破。鲁迅的《阿Q正传》写一个底层农民在革命浪潮中被作为替罪羊而枪杀,却名之曰“大团圆”,就是对历史上“大团圆”结局的讽刺。当然,社会思想的发展总会有起伏,十景病和团圆梦,也不会因一篇小说的突破而真正结束,还需要后人不断的努力。
只有直面人生,才能远离十景病和团圆梦;只有远离十景病和团圆梦,中国的文艺才能真实地反映人生!









